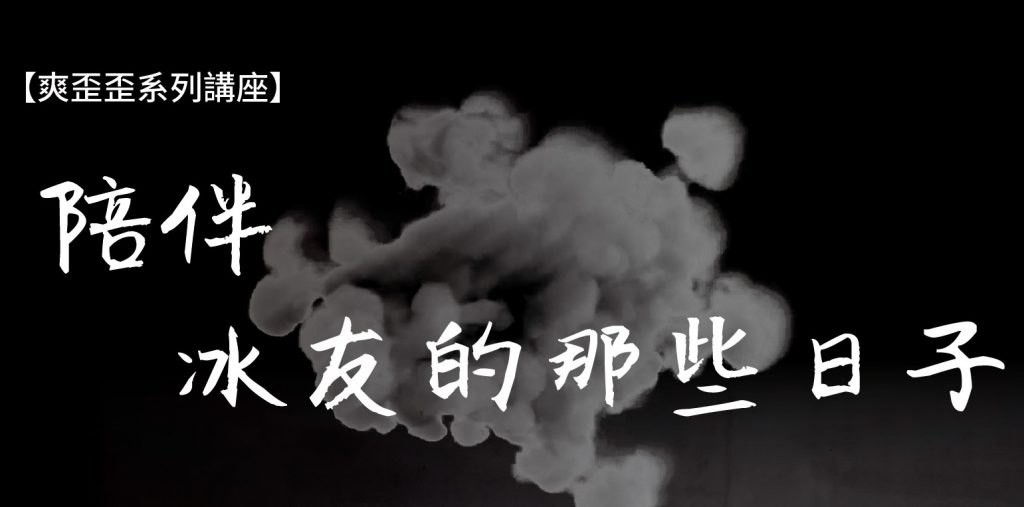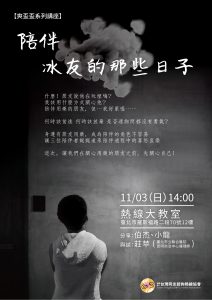文:楊剛
時間:2021/4/24(六)
分享:嗶嗶、Shun
主持人:Steven
同志諮詢熱線愛滋小組四月爽歪歪講座的題目是「是誰攻擊了我的真心」,由於「受騙」的樣態非常多元,分享者自身的經驗與應對方式不一定適用於其他人;本場活動除由兩位分享者講述在網路交友的時代自己「被騙」的經驗之外,也鼓勵參與者在以較為互動式的多個分組討論環節中分享自己的經歷、思考自己會如何應對、並且想想可以如何陪伴遇到這種事情的朋友。
由於在交友軟體盛行的時代,關於金錢的詐騙最為常見;本場活動將「與金錢相關的受騙經歷」列為最先討論的主題。分享者講述自己在交友軟體上被騙錢的經驗,包含常見的用盜用的照片並用電商投資、比特幣等等誘騙受害者匯款等等。除了要求對方買遊戲點數或是買東西,Shun 也曾經遇過對方趁自己洗澡時偷錢。在討論時,參與者討論到應對措施,包含將自己的貴重物品帶進浴室、或是邀請對方一起洗澡等應對方式。
在下一個環節,分享者討論了自己經歷到對方盜用照片、甚至是自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拍攝等等與「照片」有關的經歷。Shun 提到自己曾經在申請加入某男同志Line群時,被要求在限定時間內需要完成各種任務,從拍攝個人照片,到後來需要拍私密照片、影片並做奇怪的動作,導致他人握有自己的生活照、私照與私密影片;雖然最後沒有收到這些影像被外流的訊息,但是這個經驗還是讓他很擔心。
分享人嗶嗶也提到自己在九年前要從高中升大學的時候所發生的事件:在當時有收到消息,表示自己與當時曖昧對象視訊對話的截圖,疑似因為曖昧對象流出,被放到外國網站 Tumblr 上面販賣。對於主持人關於是否可以報警處理的提問,分享人表示很多其他受害人也有報警,但是由於不是公眾人物,並不會受到很大的重視。分享人提到,除了是個熟悉法律程序的「訟棍」,網站經營者也因為高中生年紀的人如果要走法律程序則會要面對讓爸媽知道、花錢跑法院、出櫃等等風險,因此特別鎖定高中生左右年紀的人下手。
在照片後,分享人與主持人也提到關於影片外流、或是約砲時對方要求留影片紀錄時該怎麼應對。 Shun 提到自己在這場講座前,就遇到因為不知道怎麼好好拒絕,所以被約砲對象錄影的事件;而嗶嗶則提到自己在高二的時候與朋友聊天時意外得知自己當時的男友在與自己性行為時其實會錄影,還會讓其他砲友(朋友就是其中之一)觀看。嗶嗶提到,在一次趁男友去洗澡時查看電腦,發現裡面有非常多以名字命名的資料夾,自己的名字也是其中一個。雖然沒有跟他攤牌,甚至還分擔家務以「證明自己比其他資料夾上的名字好」,在分手前還是去了對方家把東西偷刪掉了。
主持人也提到自己高二、高三時與一位對象發生關係時對方表示想要拍照,並表示會在修圖完成後將照片傳給他;但詢問數次對方仍沒有把照片傳回來,還是有感到受傷及不愉快。
接下來的環節討論了在交友時,應如何避免或應對想做出預期外行為的約會對象?例如分享人提到有遇到在前一天晚上還很正常的性行為對象,在隔天早上突然變得很暴力、不戴套硬上的事件。參與者也有提到自己遭遇以「同志按摩私約」為幌子的恐嚇事件,也就是將受害者約在便利商店,誘騙對方購買遊戲點數、ATM 轉帳,或是透露銀行帳號、身分證字號等個資的手法;若被害人覺得不對勁想要離開,甚至會用「黑道已經知道你的地點了」這種說法逼受害人就範。
活動最後,熱線的工作人員小杜為大家整理了一些注意事項:
關於金錢財務的部分,小杜建議去別人家時不宜帶太多錢,即使沒有錢,皮包也避免讓別人輕易接觸,避免個資成為往後對方要脅自己的工具;在習慣以照會友的男同志社群,要注意避免讓自己的臉、身材、私密部位出現在同一張照片裡。
小杜也提到,關於「是否要找警方」的煩惱,可以與一些和社群網站已有合作關係的 NGO 合作,以使社群平台下架你被流出的照片,或是避免你的照片被上傳。
最後,小杜提醒拔套等行為已經構成妨害性自主;如果被迫發生危險性行為,可以在 72 小時內吃 PEP (事後預防性投藥),以避免 HIV 感染。如果遇到這種事件,也可以報警給較有經驗與專業的分局或婦幼隊,或是透過 113 、現代婦女基金會、勵馨基金會等等的途徑得到社工或是法律途徑上的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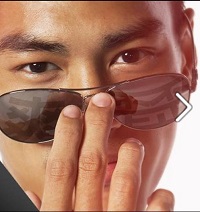 延伸閱讀
延伸閱讀
想了解什麼是PEP (事後預防性投藥)嗎?→什麼是預防性投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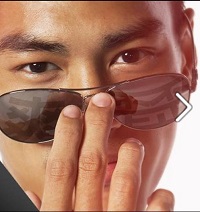 延伸閱讀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