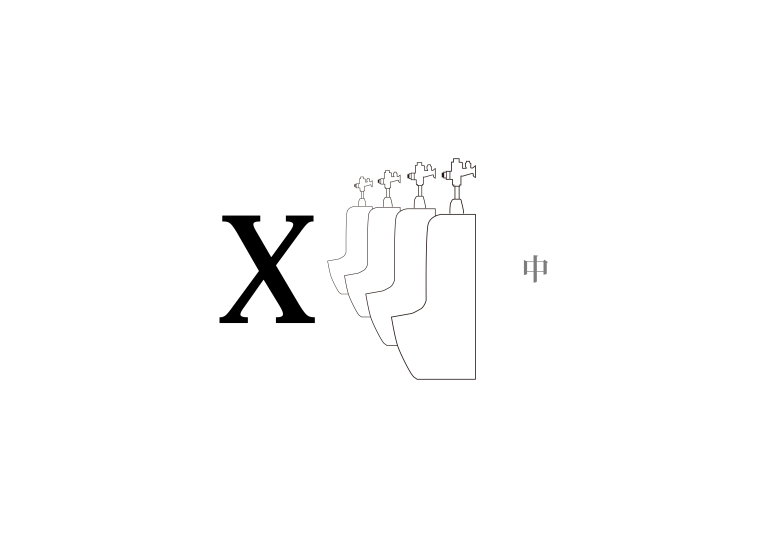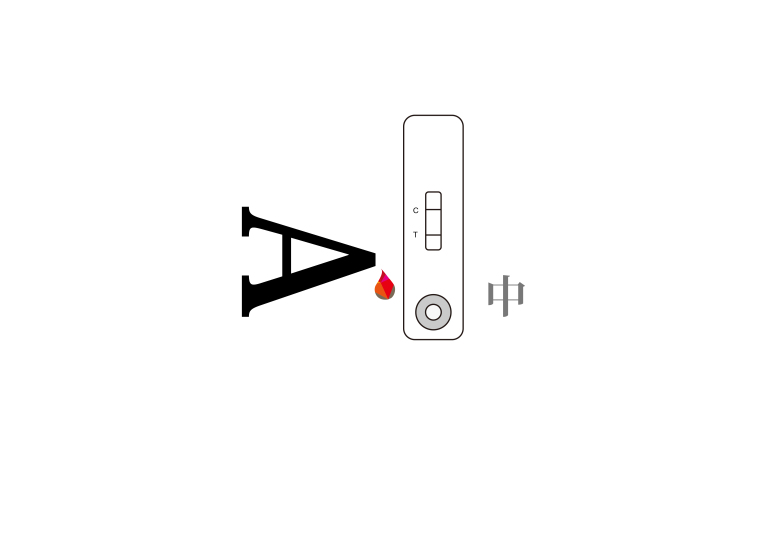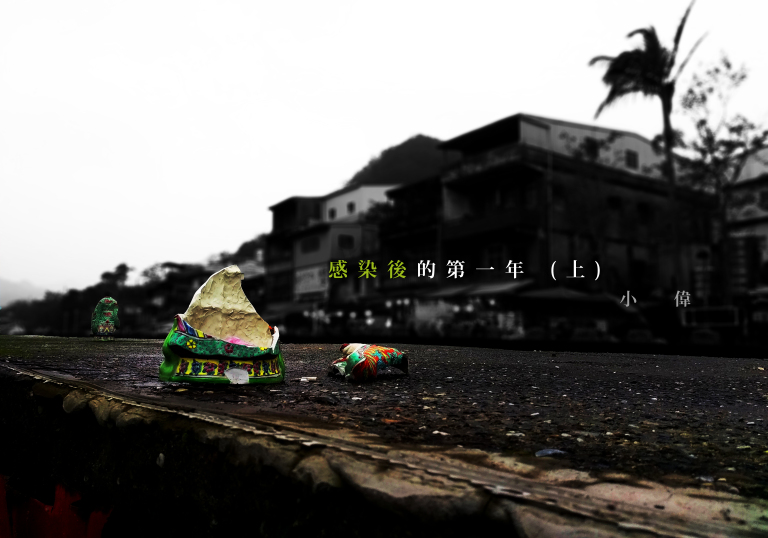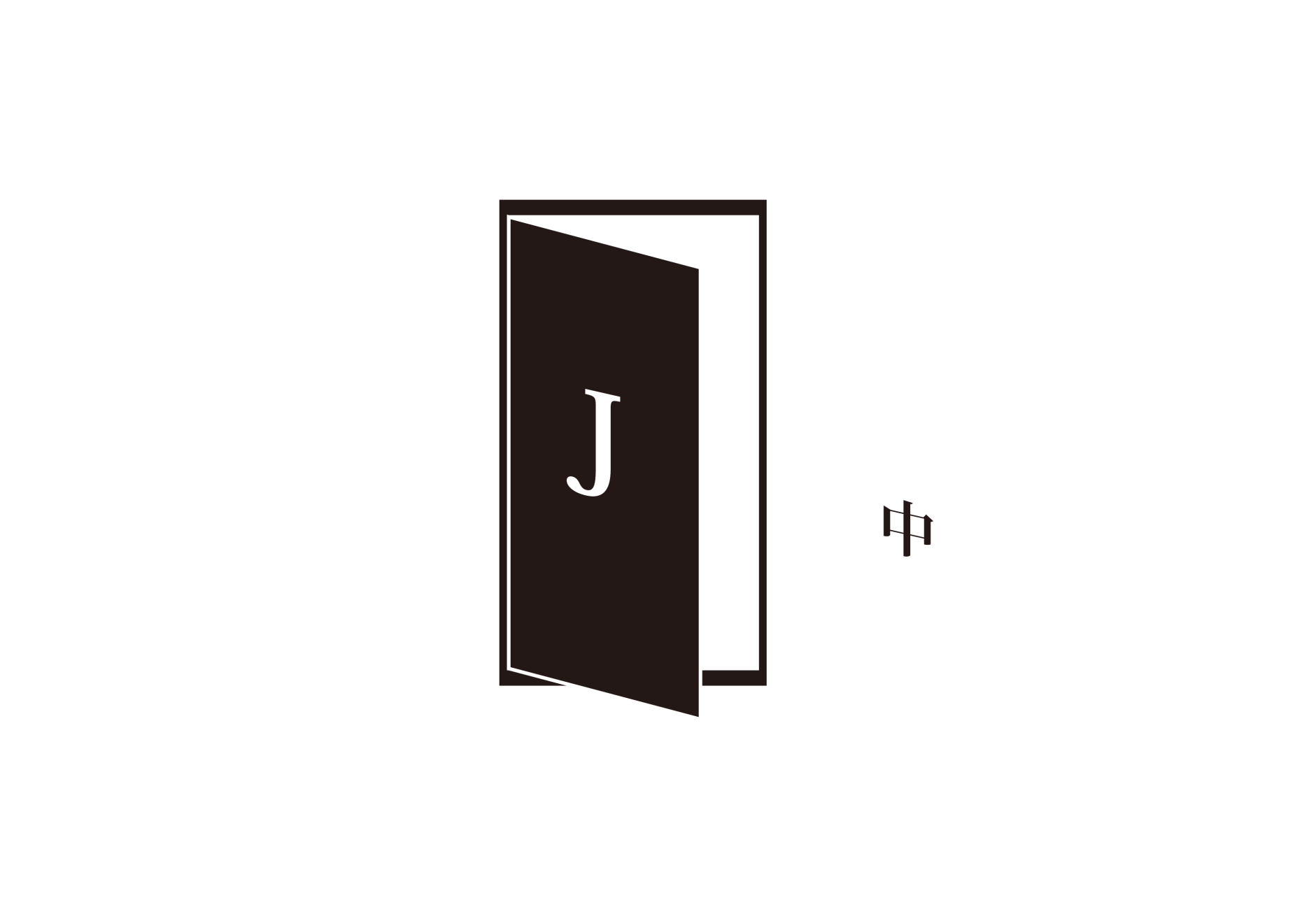圖說:捨不得明明很怕針的你,卻得抽這麼多管血;每次扎針都像是刺在我的心上一樣令人難受!
作者:藍色的夢
「同性戀就是父母上輩子造孽,才會生下這種怪物。」看著你母親在我分享有關同志議題的貼文上留言,我的心情既難過又氣憤,更怕你看見這段話;耐著性子一來一往地回應她的我,帶著「有誰敢欺負你,我一定會擋在你前面,跟他拼了」的心情,想要保護你不受任何傷害…然而我也知道,光憑我一人,是阻擋不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惡意。
兒時感情非常好的我們,一起玩耍、分享心事;長大後我們各忙各的,漸行漸遠。許久未連絡、人在國外工作的你,突然傳訊息跟我約回國要碰面時,我很開心、但也有些忐忑;猜測了幾個可能邀約見面的理由,你都否認了,那時,我已心理有數。
一見面,你遞上了血液檢查報告要我自己看,然後抱著我哭了;HIV+這幾個字,第一次離我這麼近;你不是我身邊第一個感染者家人/朋友,可是你是我最親近的人。理智告訴我,我必須冷靜,我忍著激動的心情,盡可能用最平淡的語氣,溫和堅定地告訴你,我會陪你。
慌亂無措的時候,感謝我身邊的感染者、社工、以及在國外做愛滋研究的友人,聽我訴苦、給我建議,很快地我手中的筆記本,已經謄寫了滿滿的、無價的陪伴者指南;有哪些資源、該如何一步步為未來做準備,在筆記上展開一條寬敞的路,也讓我的心情安穩下來,有能量持續陪著你。
接下來,是一次又一次地上醫院,嘗試藥物、觀察副作用、抽血,那段時光彷彿永無止盡的循環;我們在診間外等候時,害怕被認出;每天等你傳訊息回報身體狀況、是否平安,知道你惡夢連連,想要放棄吃藥…為了體會你吃藥的感受,我買了一大罐健康食品膠囊,強迫自己和你一樣,每天照三餐吞藥;只不過一個禮拜,我已忍耐不了,更不用說,對你而言,藥物是非吃不可,沒得選擇。
有人說,愛滋感染者就像是得了慢性病一樣,只要按時服藥就好,但我們都知道事情並不只是這樣;無形的眼光評判著一個人的性傾向、性生活,更無形的是被無知放大的恐懼。
前一陣子和你聊天,得知原本會定期洗牙的你,從感染之後,就再也沒去看過牙醫;更選擇了不再認識任何朋友,用封閉自己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的不友善;我能體會你心中的害怕與鬱悶,那其中當然有許多心疼不捨,但同時也為你感到驕傲,因為你選擇了讓自己感到有成就感且自在快樂的生活方式,雖然不必然是對於控制病毒量、健康狀態最有利的路,但,卻是你思考過後勇敢的選擇。
我很清楚,所有的安慰、鼓勵,都只是站在旁人的立場所給予的打氣與支持,然而,真正面對這一切好的、壞的,那個站在陽光下/或者風雨中的人,是你,一個人。我只能一而再地在你身邊告訴你:「我會陪你、也謝謝你願意讓我陪著」,除此之外,我希望我有力量,能讓陽光在和煦一些、讓風雨漸歇,好讓
身處其中的你,能夠感覺好過一點。
不擅言詞的我,每次陪你看診都覺得把氣氛搞得很冷、很僵,但,我很愛你,我會用行動與陪伴來實踐這說不出口的愛,希望你也接收得到!
…